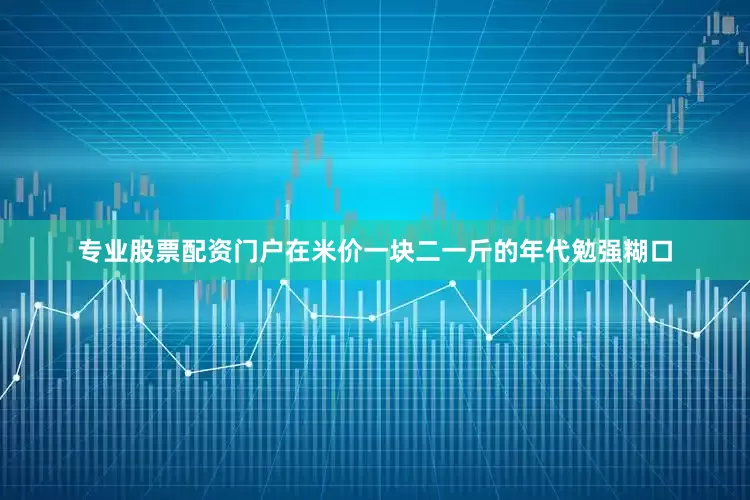
“1990年8月,南京玄武湖边。”老人抬头笑着说:“菜市场几点关门?得快点,不然便宜菜要被挑光喽。”摊主愣了愣,小声嘀咕:“这不是当年南京军区的丁司令吗?”老人摆手,“别提那些旧事,叫老丁就行。”简单几句,把他的晚景勾勒得分外清晰。
丁盛1913年生于湖北黄安,17岁走进红一方面军。当过连长、团参谋长,抗日战争里带队血战,解放战争时在四野穿插千里。1950年,他的54军首批入朝,临津江畔那一仗,炸毁美军坦克九十余辆。国内许多人提起那段历史,都会把丁盛与“敢打硬仗”划上等号。

战争胜利后,军衔授予时他是少将,却颇为特殊。别人安稳进军校深造,他接连被派去最艰苦的前线:1959年藏区,1962年中印边境。54军在东山口正面突击,中方伤亡极小却拔下印军主要火力点,丁盛在总参作战简报被点名表扬。有意思的是,标准的四野作风里,自带一股不服输,正是这种性格埋下日后沉浮的伏笔。
1968年2月,他升任广州军区司令员。当时文革风暴正盛,诸多将领陷入漩涡,他反而“靠前指挥”连续稳住两广局势。一年之后,他又挂上“四个第一”,同时抓广东省委与军区。外地干部初到广州常自嘲:“这片地界儿,谁不先去见丁司令打声招呼?”然而仕途高峰仅维持短短几年。
1973年底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,同年冬至,长江大堤北风凛冽,他在军委碰头会上强调“战备不能松”。消息传回部队,官兵们说:“老丁还是那个‘冲锋号’劲头。”可惜政治气候骤变。1977年,因牵涉某些事件,他被暂停职务,随后离开南京东郊的青山口营区。
1982年,组织部门将他安置在南昌地方干休所。表面上是休养,实际与原部队彻底脱节。制度上,一旦军籍暂时冻结,供给需地方解决,待遇层级立刻滑坡。150元月生活费,在米价一块二一斤的年代勉强糊口,更谈不上保姆、秘书。熟人探望时偶尔打趣:“丁司令何不写信反映?”其实他写过,可信一到北京就石沉大海,他索性不再开口。
日子清苦,却见本色。南昌到南京千余公里,他独自买了硬座票,挤夜车回家。到站时,列车员提醒:“您岁数大,换软席吧。”老人咧嘴:“掉几颗牙,腰还挺直,硬座不碍事。”那年已是71岁。
家里人口不多,老伴身体也不好,买菜做饭落到丁盛头上。玄武湖附近的朝天宫菜市,每晚七点后菜价大跳水,他掐点去扫货,一篮空心菜两毛钱,还要挑老嫩适中。有人认出他,敬个军礼喊“丁司令好”。他赶忙摇手,“退了,退了,买完菜得蒸米饭,别误事。”
值得一提的是,他对昔日部下从不摆架子。某次陆军学院几位年轻学员偶遇,敬礼后自报家门:“54军后续队列。”丁盛却问:“你们班里体能谁最好?”几个小伙子被问懵,看着这位满脸皱纹的老人,立正回答:“报告首长,全部达标!”丁盛点头:“能打,别骄傲,别学我年轻时那股犟劲。”一句玩笑,带着浓浓口音,学员们一直记到毕业。

然而健康并不配合。1991年伏天,南京气温逼近40℃,老宅没有空调,他心脏病复发。送往鼓楼医院途中,护士轻声劝慰:“您别担心,部队医生马上到。”他闭目摇头:“不麻烦他们,我就一退休老干部。”抢救后转危为安,可那次病倒彻底暴露了现实:没有正式的军队抚恤,医药全部走地方统筹,一张手续要跑四五个部门,很折腾。
1995年7月,中央军委下发文件,解决文革历史问题的干部统一落实离退休待遇。丁盛的名字终于重新归入军籍序列,移交广州军区干休所,级别定为正师。消息传到南京,他苦笑:“头上军帽戴了半生,终于又回来了。”搬迁那天,下着小雨,他拄拐杖站在院门口,同邻居握手,“南京这座城给过我家一样的温暖,常来广州玩。”
干休所条件显然不可同日而语,有单独套间、军医巡诊,伙食按部队标准配给。老战友余秋里来看他,门口两人一番调侃。余说:“司令住师级房,亏不亏?”丁盛回句湖北土语:“天大地大,能睡踏实觉就值。”多年颠簸总算告一段落,可时间已不宽裕。1999年11月,心衰并肺部感染,他病情恶化,医嘱无法再拖,抢救无效与世长辞,享年86岁。

梳理丁盛的后半生,几组数字特别醒目:54军、150元、1995年、86岁。数字背后是一条坎坷曲线,映照出那个时代不少将领的共同命运。政策风向改变,个人际遇瞬息万变。有人好奇,为何他始终不言怨?答案或许在玄武湖边那句轻描淡写的“买完菜得蒸米饭”。能够自理,就有尊严;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,便保住骨子里的硬气。
不得不说,与其把丁盛看作传奇将领,更像一面镜子。它提醒后人:功劳簿不等于终身免检,荣誉也无法抵御忽然而至的落差。真正支撑他的,是早年穿越战火积淀的坚韧。哪怕提着篮子挑便宜菜,也不改那份坦荡。至于别人怎么称呼,他只留下一句话:“叫老丁!”
2
易云达配资-易云达配资官网-在线股票配资-配资门户首页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